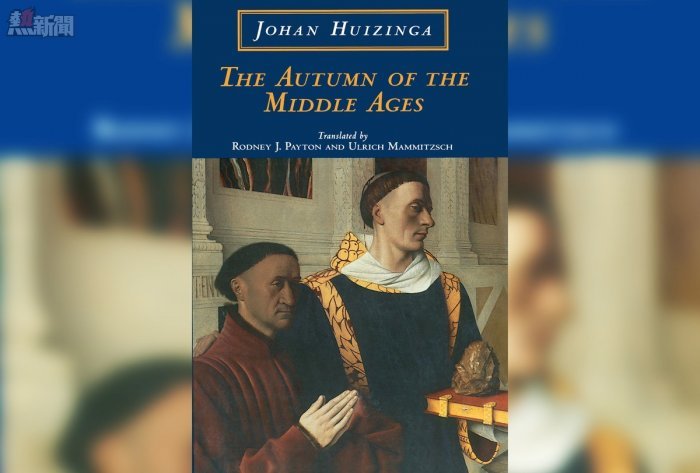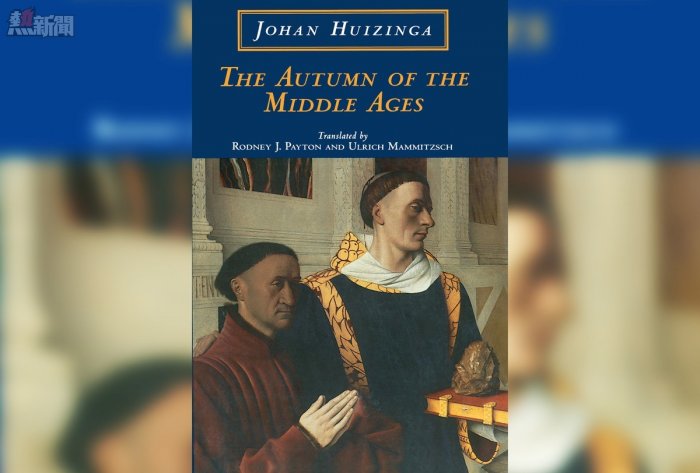
有多少種理解世界的方法?又有多少種表達心中世界的方式?我還在收集各式各樣的答案,路途上偶而會碰到有趣的人,他們告訴我很多獨一無二的故事,體現他們對這世界的想法,但更多時候人際緣分可遇不可求,我只可以埋首於書海,耐心翻卷揭頁,期望搜索到那些彌足珍貴的答案。
讀畢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所著《中世紀之秋》(The Autumn of the Middle Ages),我忍不住想這個問題:如果我們生活於一個衰敗的年代,那個世界會是怎樣的景象,又會為我們帶來甚麼感受?
腐敗與驕奢,戰亂與瘟疫,無理災厄不斷衝擊14至15世紀勃艮地和法國,於那段所謂中世紀之秋的歲月,我們日後稱作「資本主義」的體系正悄悄成長,金錢、商人與銀行家等待著革命的機會。不管是否洞察到大歷史的轉向和發展,或多或少,貴族、教士、教士、編年史家、詩人和畫家都意識到一點:他們的世界正邁向終結和毀滅。
貴族的幻夢劇場
無力改變終將消逝的命運,貴族投入追逐榮耀與愛情的幻夢劇場,他們穿上誇張失實的服裝配飾,於不斷增生的繁文縟節中,一絲不茍地反覆確認自身地位;他們跟從永不饜足的虛榮心,排練騎士決鬥的戲碼,效忠可望不可即的女神,捲進無休無止的家族仇殺。
貴族們不是不知道,冷酷狡猾主導他們的世界,色欲與殺戮無所不在。他們不時自嘲虛偽的光榮,坦承為掩飾華衣美服下的獸性本能,創造各種各樣的借口,但除此以外還有甚麼出路呢?歸隱田園過簡單生活,說得夠多夠厭煩,幾乎成為虛偽掩飾的一部份;虔誠向上帝懺悔認罪,這已是劇場生活的一幕,天主沒有令任何人能夠抵抗欲望與誘惑。
信仰的極致和終點
在這惡貫滿盈的世界,教士們對人類墮落痛心疾首,但他們最擔心的還是世俗羊群的庸俗氣息,玷污上帝真理的神聖。當市井百姓拿上帝的養父約瑟開玩笑,用他來嘲笑不幸「戴綠帽」的丈夫,每位聖人都難免沾上凡塵俗氣;當村婦愚民為求生活幸福安康,爭奪聖人遺骸,扯得屍身七零八落,聖物已走進異端魔法的境地。
在中世紀某個秋日,異地來的朝聖客一雙一對趕赴幽會,商販、乞丐和妓女如常在教堂開檔做生意,教士感慨普羅大眾太過虔敬上帝大能,聖經話語已完全滲透日常語言,就在信仰完全消融於生活的一剎那,上帝自身失去超越神秘的魅力,只剩下禮儀的軀殼,無奈接受發自極致信仰的不敬和褻瀆。
剛巧於那個秋日,教士內心也是鬱悶迷惘,他們曾經費盡心神,從世間一事一物尋找上帝蹤跡,動用所有想象力,挑選最貼切適當的象徵,描畫上帝的理想國度,白玫瑰是虔誠與聖潔,紅玫瑰是熱情與奉獻。數百年過去,教士卻差不多耗盡想像力,完美漂亮的象徵系統日漸失去養份,只可以依賴昔日貯藏,重複吐出經已枯燥繁瑣的措辭。
這時候,教士索性讓美德與罪惡直接化身為人物,故事中名叫「理智」的老師教訓名叫「熱情」的學生;他們還從聖經裡挖出神秘數字,炮製七罪八福,總之用最懶惰的方法宣揚聖經話語。可惜他們有一批同僚卻無法欺騙自己,決定勇敢面對現實,承認人類話語和智慧有窮盡,永遠無法理解和描畫上帝這無限存在,這消頹放棄的態度最終引導出佛家的結論:上帝是空無。
衰朽大樹上的爛熟果實
尤如衰朽大樹上的爛熟果實,儘管藝術與史學蘊含美感與故事,但都只是印證貴族與教士的枯竭靈感,無法孕育全新思想主題的種子。流暢詩歌與浩繁編年史不厭其煩地延續某幾組比喻,鞭撻齷齪卑劣的時代,嗟嘆現世生命的無用,歌頌英雄的璀璨榮譽與純潔愛情,嚮往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
如果說文字可以不斷滋長纏擾,直到完全毀壞講究完整與平衡的美感,畫家從一開始便受到眷顧,他們必須於畫框內表達一切,不得不仔細挑選素材,考慮構圖的穩定統一,於是有意無意間留下傑作,成功駕馭那時代作狀繁瑣的比喻和象徵,呈現後世能夠理解以至感受的美感。可是畫家自身卻不一定注意到這一點,純粹美感還是個陌生概念,他們只想運用高超技藝,取悅貴族與教士主顧,以最優美的方式滿足喜好奢華的視覺欲望。
與其說中世紀之秋是個絕望的年代,不如說那段時光浮現更為深沉的苦悶,俗世人類已經耗盡所有精力,等待死亡與天國;與其說好戰貴族和腐敗教士摧毀中世紀世界,不如說精神苦悶與想像力乾枯才是終極折磨,誰都再沒意願尋找出路,只能於囚籠裡互相苦笑凝視,等待終局來臨。
作者:鄭子健(本文章由聚言時報授權提供)
讀《中世紀之秋》:致那衰朽爛熟的時代(鄭子健)
https://www.facebook.com/GaldenPolymer/time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