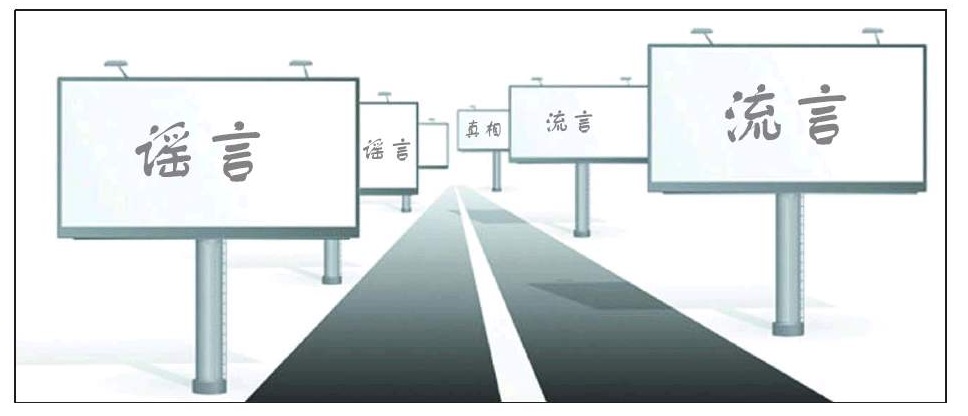當人們談論自愛、自尊、驕傲和虛榮時,就好像這些詞可以互換。所以更不用說盧梭哲學概念里的「自尊」,以及自負、自我沉溺、自戀等概念的細微差別。我們可以用以上任何詞去形容以「我」為中心的一代,或是咄咄逼人的政客,或是自拍成癮的現象。但是這樣就忽視了這些概念的重要區別,很可能將人類「自我」世界的精彩紛呈變得平淡無味。
英國詩人約翰·彌爾頓為討論這些概念開了好頭。他正確地以為,那個「虔誠的、光榮的自我」對我們至關重要,是「我們追求一切崇高事業的進取心的源泉」。1642年,在一篇關於教政的文章里,彌爾頓呼籲人們要有足夠的自愛或自信,從而在改善自己和他人生活時,能更好地發揮作用。這種自愛和自信,少了的話,會使我們在真正需要做什麼時,畏懼不前;多了的話,則會開始做一些並不適合自己的事。
彌爾頓所說的是適度的自信,其程度恰好足以給予我們勇氣去面對困難,解決問題。今天,我們可能會說,要有適度的自尊,並使其成為良好教育的一個目標。但是這裡,我們需要加一個亞里士多德式的警告。自尊之「尊」,其背後的根本思想,是一個關於「估計」的問題。幾乎所有情況下,我們都最好不要對事物預估過高或過低,而對自我的估計亦是如此。如果我將自己的許多方面都過高估計,那麼很可能遭遇挫敗。比如,我認為自己是個很棒的登山者或騎手,而事實上,自己並沒那麼好。這隻是個比方,或許我對自己的其他方面都有這種誤解。
那麼,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大眾眼裡,自尊心強是一種所謂的美德,一個極其溫暖舒適的保護層。比如,傷害孩子的自尊,通常被看作是僅次於嚴重濫用職權的罪行。但是,如果讓一個孩子相信她自己是個很棒的足球運動員、小提琴手或數學家,而事實她並沒想象的那麼優秀,那麼很快她將面對的是迷茫、失望、甚至怨恨。而這裡,對於無能的家長或老師隱含着一種諷刺。他們不顧一切地「慫恿」孩子,不斷告訴孩子他們可以做得更好(「虎媽」綜合症),或許可以增強孩子的自尊心,但至少也同樣可能鞏固這種方法的弊端。當孩子遭遇失敗時,一切化為泡影。如果在大英圖書館書目中搜「自尊」一詞,會出來一萬多個結果。最早的一本是1869年的,書名很有趣,《對自尊的譴責》。而在這本書出版之後出現了巨大空白。直到1969年,這一領域的研究才真正出現繁榮。這些書中有多少着重討論了亞里士多德哲學所指的兩面(譯註:過多或過少)分別隱藏着什麼危險?這將是個有趣的問題。
如果自尊從總體上來說被高估,那麼驕傲——根據基督教傳統,是所有罪行的根源——並不常被讚揚,除非我們是為他人驕傲。然而,也的確有合理的驕傲:比如一個人做了好事,或迎難而上而獲得成功,或至少具有某些受人尊重和敬仰的品質,而因此感到快樂。這種驕傲能使我們不對自己失望,最好的情況下,它能確保我們以受人尊重的方式,好好做事。而當驕傲傾斜為一種自以為是的自我優越感,就會變得冒犯。自以為優於他人,並隨之而來對他人的輕視:簡單來說,就是傲慢。這種驕傲把我們帶到了過度自愛的極端情況,自戀。
不過,到底該把虛榮放在哪個程度呢?驕傲的人會因為做了值得讚賞的事而感到快樂,而對於虛榮的人,讚賞本身成為了目標。虛榮心對他人的讚美是貪婪的,不管這種讚賞是否名副其實:虛榮的人喜歡被吹捧,即使吹捧本身很虛偽。虛榮通常是自尊心脆弱的結果——害怕別人看扁了自己,導致自己不斷尋求定心丸。如此說來,虛榮心通常更容易成為同情、而非譴責的對象。對一些青少年來說正是如此。他們如此沉迷於將自己的生活細節或自拍發在社交網絡上,期待着朋友們在下面歡呼點贊。我們可能注意到,適當合理的驕傲,會成為虛榮的絆腳石,因為它能阻止人們墮落到向人索取讚揚或恭維。
自尊、自負和自戀
18世紀50年代,讓·雅克·盧梭普及了「自尊」(amour-propre)這個詞,用來指人們關心自己與他人比較而言的地位或位置。在過去,這可能是相互攀比的問題。而今天,更像是我們執迷於將自己吝嗇節儉的生活與想象中的名人生活相比較。對盧梭而言,這一類擔心不可避免地被虛榮心毒害,但更糟的是,它通常還伴有鄙視(向下看)和嫉妒(向上看)。他認為,這種擔心,「如果只存在於我們自己的估計中,則一定會造成對那些質疑我們成功的人一定程度的憎恨」。這也許不錯,但對於那些競爭力相對較弱的人,這隻會帶來沮喪的情緒,覺得自己的生活相當悲慘。
盧梭總是不知疲倦地聲討「自尊」的邪惡之處。在他的那本對教育學頗具影響的《愛彌兒》中,他謹慎地概括出如何培養模範子女、並使其免於這些邪惡的方法。他眼中的理想學生,是立志要堅決避免與他人的任何比較的。
儘管盧梭告誡我們要遠離鄙視或嫉妒,這無可厚非,但是他或許誇大了完全獨立的益處。因為一個人做了好事並且適當地感到驕傲,是情有可原的。這也意味着比自己預期要做得好,反過來又隱含了與他人眼裡的正常水平的比較。只有當你的游泳或跑步技能多少高出正常或平庸水平時,你才會感到驕傲。我們是社會的人,是一群社交動物。哲學家們早就發現,人們互相是對方的鏡子,而且當我們發現在他人眼裡,自己並不是自己期待的那麼好時,我們會輕易受傷。大衛·休謨在他1739年的《人性論》里,給出了一個現實的例子,「當你告訴一個人他有口臭時,他肯定會感到羞辱,儘管對他自己來說並不是什麼大事」。盧梭忘記了對於這類事情,用亞里士多德主義解釋的優勢:個人對自己地位的意識只需一點點,而不要太多,這才是理想的。
如果說虛榮心是對他人讚賞的過分在意,且通常起因於更加根本性的不安全感的話,自負則把我們帶到另一個方向。自負是對自己有足夠高的評價,以至於不需要他人的讚賞。自負者對自己相當肯定,使其不需要從他人那裡再次得到確認。這從某種意義上令人反感,因為虛榮心並不始於自負者告訴你「你不重要」;事實上,你對他來說一錢不值,他完全忽略你的聲音。自大、頑固、過度的自信和傲慢,都是自負的特徵。這是政客們的典型嘴臉,被阿諛奉承者們環繞,永遠是讚美的中心,還常常自以為是地相信自己的領導力、智慧、見地和能力。
終於,我們該討論自戀了。自戀意義中的自愛排出了其他一切社會情感和擔憂。自戀者並不像自負者——自負中含有對他人的傲慢或鄙視,就像唯我論者,或是覺得全世界就他一個人。這就是為什麼在希臘神話中,那耳喀索斯能聽到的唯一聲音是來自水澤神女厄科(Echo,字面義為「回聲」),即,他自己的回聲。他眼中沒有其他人,也聽不到其他人。我們也知道,故事的最後,那耳喀索斯的目中無人為自己挖了墳墓。他自我沉溺,無法自拔,生不如死。
那麼在當今世界,以上癥狀里哪個最突出呢?哪個最讓人感到可悲呢?我所說的自負,或狂妄的自信,顯然已經蔓延于政界,但也侵蝕了商界。學術期刊《心理學,犯罪與法》刊登了2005年的一項調查:調查針對英國頂尖的商業經理人;結果顯示,他們在各種關於精神病人格障礙的測試中所得的分數,高於從布羅德莫提取的樣本——布羅德莫是英國關押精神病罪犯的最主要監獄。根據這份報告,「從癥狀描述層面來看,這些測試結果可以理解為職業經理人的膚淺魅力,缺乏真誠,自我為中心,控制欲強(裝腔作勢),誇大其詞,缺乏同理心,利用他人,獨立性(自戀)……頭腦僵化,頑固,愛發號施令(強迫性)。」
當然,強迫性專斷傾向和其他類似癥狀在人類歷史上並不鮮見:不論是斯大林,還是1987年諷刺電影《華爾街》里的哥頓·蓋柯——「貪婪無害」文化的倡導者,在卡里古拉和成吉思汗的眼裡,一定沒什麼了不起的。但是他們都很可能一直是局外人:沒有很多人能像他們這樣,而且我們沒有理由去判斷他們在社會中所代表的意義比曾經更大還是更小。
人的本性
理論家們在理解「人的本性」這一概念時,並非都信心十足,特別是當它被解讀為所有人類所共有的一套心理傾向時。然而,大多數人會同意的是,在歷史上,這類本性並不曾發生重大改變。人類進化歷程還太短,不足以將我們與祖先放在完全不同的模子里。
但是,在不同情況下可能發生的改變,正是我們通常對彼此的期望。比如,文化的改變能夠解釋為何我們不同於過去羅馬運動場里嗜血的觀賽者,或是英國攝政時期的享樂主義者,亦或是19世紀馬塞諸塞州的嚴格先驗主義者。所以,一方面,聲討虛榮、自負、自尊或自戀是簡單;但另一方面,若是探討我們今天這個時代到底如何形成了一種氛圍,讓以上這類特徵以各種形式存在,可能更有啟發意義。如果整個社會歌頌財富,那麼只有財富能滿足虛榮心。如果社會歌頌的是慈善或公共精神,那麼虛榮和驕傲都會向這些美德看齊。如果社會讚美和羡慕名人,那麼一些沒有足夠驕傲或自尊的人會幻想成為名人,並對自己平淡的生活產生不滿。
若從這個角度來看,則當代文化並沒有那麼令人樂觀。如果人們能認識到,社會地位只因品德而不同——正直,勇氣,能力,善良,公平,智力——這才是鼓舞人心的。而且名人和財富不能成為這些品質的替代品。當然,如果有人說能的話,那麼他們肯定是強調名人成功所需要的品質,從而名人的社會地位便體現了他們的所值(「因為這是我應得的」)。如此一來,達到這種地位所需要的支持,或是爬上金字塔尖所需的聰明詭計,亦或是純運氣,都被人們悄悄地遺忘。
如果文化能朝一個方向轉變,那麼它也可以變回來。我們是否能想象一種逆轉——某種近似於社會契約的東西,或是對公共精神的感知、對不合理花銷的鄙視、對粗俗展示的尷尬,或僅僅是想要低調離場——讓這些來主導我們對自己和他人的期望。畢竟我們知道,在有些文化里,大聲呼喊自己高人一等的行為是很糟糕的。
但或許最重要的是,我們應該鼓勵一種愉快的、顛覆性的嘲弄精神。如果沒有多少東西比自戀者的自大和傲慢更糟糕的話,還會有什麼比虛榮的表現更荒謬的嗎?虛榮這個詞本身就帶有譴責意味(「虛榮」的拉丁語語源表示「空虛,虛無」)。我們可以學着不去在意表象,不去渴望得到他人的讚賞。我們甚至可以學着少發一些自拍。
From AEON
為什麼我們應該學着少發一些自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