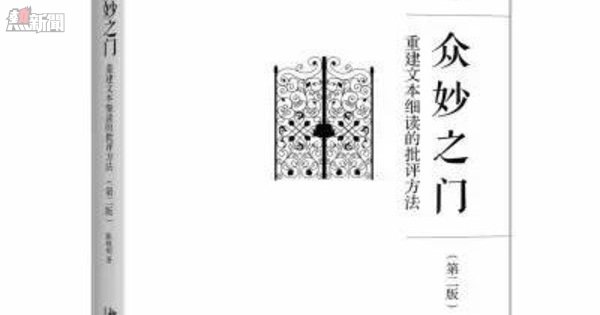


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與批評,並沒有真正完成現代理論批評的轉型。80年代至今的批評模式,即感悟式的、印象式的和論斷式的批評文體還是今天的主流,還沒有經曆過文字細讀的全面“洗禮”。在當今中國,加強文字細讀分析的研究顯得尤為重要,甚至可以說迫切需要補上這一課。
強調文字細讀這種批評方法,是有一個前提,即把文學作品看成是語言的構成物。這似乎是個常識,任何閱讀文學作品或研究文學作品的人都會把文學作品看成語言的構成物。但實際上,是把文學語言看成一種承載思想內容的工具手段,還是看成是語言本體,二者對待文學作品的態度並不一致,所採取的文學批評方法也不盡相同。把語言看成表達工具或手段,當然也沒有錯,文學作品的語言主要是用於表現社會曆史及現實的內容,思想內容是決定性的,語言則是次要的,甚至是可以被忽略的,所謂“得意忘形”“得魚忘筌”。而強調文學作品是語言的構成物,並且在語言本體的意義上來理解文學作品,這顯然是十分重視文學作品的語言特性,也對文學作品的語言提出了較高要求。這也導致了隻關註文學語言本身,把文學作品的意義看成是語言修辭的結果。
歐美“新批評”把文學語言的重要性強調到最為重要的地步。“新批評”之重視語言,大抵有二個原因需要考慮,其一,“新批評”研究詩歌,詩歌的語言無疑是重要的,也是要經得起細讀的;其二,“新批評”興起於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的英國,而英語文學在一戰後迅速在世界範圍傳播,英語很快成為國際化語言。英美的“新批評”對英語詩歌的細讀充分發掘了英語的語言魅力,德語的繁複和法語的微妙都沒有英語的簡單明瞭更便於傳播和交流。固然不能說“新批評”這種批評方法是配合了英語國際化(另一種說法是英語的文化霸權)才產生影響,但“新批評”的細讀方法無疑使英語文學的語言魅力得到了極大釋放。
既然文學作品的語言如此重要,那麼,也就意味著文學作品具有本體性質,在語言的事實中就可以解釋作品的一切。作者的支配權也就變得無足輕重,因為“誤讀”本身也能釋放作品的更多內涵。“文字”這種觀念就更加明確地確認了作品本體的自主性。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從作品到文字”的觀念被視為文學理論批評中最富有挑戰性的變革,法國理論家羅朗·巴特認為,文字這一概念不僅與言語中心主義對立,也與傳統的作品觀對立。傳統上的作品是指相互分離的裝訂在書皮之間的實體,並被編入圖書館的書目。新的文字則被看作是語言活動的一個領域;亦即一個文字總是和其他文字關聯,總是互為文字,文字之間可以構成語詞的和修辭的遊戲。在這種文字觀念下,羅朗·巴特和米歇爾·福柯順理成章地提出了“作者之死”,其實就是把文字提到自主的地步,讓文學批評回到文字,以語言細讀分析為依據,建立起一個獨立自主的文學世界。
羅朗·巴特是一個文字批評的大師。“新批評”的理論家們還是在詩歌裡討生活,詩的語言精緻、凝練,可以經得起細讀,其中的隱喻、換喻、轉喻之類的修辭關係就足以把字詞的文學魅力體現得淋漓盡致;對於小說這類敘事文字來說,如何分析則顯出了難度。巴特硬是就巴爾紮克的一篇短篇小說《薩拉辛那》寫了一本書《S/Z》,這就顯示出細讀的功夫。顯然,巴爾紮克還是現實主義作家,並非在語言和表現手法方面挖空心思的先鋒派作家,但對於這些文字批評大師來說,僅僅依憑文字的語言機製就可以讀出無窮無盡的思想,可以連線起其他文字的內容。美國“耶魯四君子”的領頭人保羅·德曼在分析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時,也極盡細讀分析的才能,從描寫、敘述,到語言的通感和換喻,以及寓言性的意義,德曼的批評無比繁複玄奧,但也正是他把普魯斯特的一部小說的開頭段落分析得如此豐富奇妙而且出人意料,著實是顯現出新的理論批評的巨大的魅力。
故而70年代是美國文學批評的黃金時代,那是以保羅·德曼、希爾斯·米勒、傑夫裡·哈特曼、哈羅德·布魯姆為先鋒的後現代理論批評。他們的批評其實是新批評傳統與解構主義觀念、結構主義敘事學、文字的修辭性細讀、語詞的智性遊戲的綜合運用,開啟了一個自由開放的批評場域。但所有觀唸的、方法的展開,都是建立在文字細讀的基礎上,它們把文字細讀發揮到極致境地,彷彿所有的觀念、方法以及細讀本身都是文字自主地迸發出來的。米勒曾經說過,對德里達、德曼、布魯姆、哈特曼這些同事最欽佩的不是他們的理論構想,而是他們對文學作品或對哲學著作具有穿透力與原創力解讀的巨大才能。米勒等耶魯其他幾位理論家,都是從文字中去發掘新的要素,打破現有的文學理論的束縛。他們對文字的每一次讀解,都是一次理論的新的闡發,而不是去證明現成的結論,更不是拿著現成的結論去套用或壓製文字。
今天中國的文學批評不可能去重複歐美文學批評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新批評”走過的老路,同樣也不可能把歐美七八十年代的理論批評作為樣板接受過來,即使在歐美,這樣一種所謂文字批評建立起來的路數,也已經完全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大而怪誕的“文化研究”——盡管它在方法論上與文字批評相去未遠,但它的主旨卻是文化政治和曆史批判。
在《眾妙之門——重建文字細讀的批評方法》一書中,我認為重提或者說補上文字細讀這一課,目的在於使中國的文學批評也能深入到作品文字內部去討論問題,把作品文字作為一個活的物件,尤其是善於發現真正有創新性的作品,能對這些優秀作品進行細讀分析,去發掘漢語文學的博大寬廣和豐富精微,這當然也有一個前提,那就是當代漢語文學有足夠的優秀之作。就像特里林所說的,“我隻談論最優秀的作品”。如果精品匱乏,或者看不到“佳作”,理論批評陷入“酷評”和“惡罵”的焦慮,也不可能投入熱情去細讀作品文字。
當然,理論批評本身要有能力,同時保持對創作的尊重,才能發現這個時代的優秀之作。如果一味拿著現成的標準框框去套新出現的作品,那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發現。理論批評只有與優秀之作博弈,真正激發和釋放作品的創新性潛質,才能完成自身的更新,這一定是理論批評與作品文字在細讀中達到一種理解、感悟,並且相互激發與創造。中國文學批評或許也能從這裡開掘出一條路徑。
《眾妙之門——重建文字細讀的批評方法》(第二版):陳曉明著;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轉載請註明出處。
Reference:健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