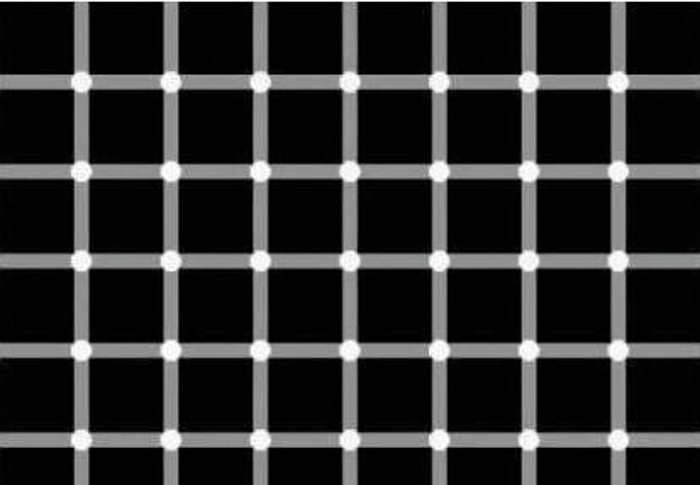如果不是讀了路內的這本《慈悲》,恐怕心中仍會時時泛起疑問:為什麽在我們的傳統文明中,對道德寄予這麽高的期望。
李澤厚先生曾把中國古代文明稱為“泛倫理主義”,即用道德來解釋一切——生活挫折了,因為壞人戰勝了好人;時代幽暗了,因為小人遮蔽了君子;天下崩潰了,是因為佞臣打敗了忠臣……總之,再復雜的現象,都能簡化為善與惡。
但,道德真的可以作為終極尺度嗎?
張灝先生曾將這種思維習慣斥為缺乏幽暗意識,當一代代哲人站在群峰之上指點江山時,他們忘了:人性中既有大善,也有大惡,那些曾建造出人間天堂的人,其實一樣可以製造出人間地獄,而忽略了內心中的幽暗,我們就會一次次在天堂夢的蠱惑下,去重復罪惡。
張灝對士大夫的“淑世精神”的批判不可謂不深入,但他忽略了:讀書人未必是承繼傳統的主體,如果沒有無數代人民執著地在堅守著“好人夢”,所謂“泛倫理主義”,也隻是空中樓閣,根本傳不下去。
為什麽我們這麽渴望“好人”?從路內的《慈悲》中,頗可見端倪:
大饑荒中,小說主角水生的父母帶著他和弟弟逃難,為了不一起被餓死,父母各帶一個孩子,分手於歧路。母親帶著水生來到城裏,卻不幸死亡,叔叔收養了水生。
成年的水生進了化工廠——因生產苯酚和骨膠,這裏臭得驚人,三分之一的工人退休不久便患癌死掉。在師傅呵護下,水生站穩了腳跟。化工廠經歷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僵死、改革開放初的勃興、股份製改造後的衰敗。雖然每次都是翻天覆地,但基本運轉規則卻依然如故——掌控資源的人,天空總是更高,而對於蕓蕓眾生,有尊嚴的活著,隻是一個遙遠的夢想。時代肆意地塗改著水生們的命運,他們太微不足道,原以為靠技術、靠體力、靠實誠就能贏得做人的尊嚴,可事實是,不論怎樣掙紮,他們永遠是玩物,是大人物擺弄來擺弄去的棋子。
水生的師傅一生助人無數,到後來,卻不得不長跪在辦公室門口,隻有患了骨癌,他才意識到:自己才是最需要幫助的可憐蟲。相比於師傅,水生更有韌性,多少挫折,他都忍了下來。但笑到最後的依然是壞人,水生們隻能咬住牙不哭出聲來。
好在,晚年的水生終於發了一點財,領養來的女兒也上了大學。但,對水生來說,這又有什麽用呢?人生最好的歲月已經過去,在給妻子骨灰盒下葬的路上,他意外地遇到了當年失散的弟弟,他竟然在大饑荒中活了下來,卻連父親被餓死的地方都想不起來了。
在這個世界上,太多人曾經活過,但他們又從沒像人那樣活過,從沒有完整地品味過一個人理應品味到的那些東西。
弟弟也是掙紮地挺過了這一輩子,晚年當上了假和尚,可廟是假的,佛卻是真的,在假戲真做中,水生的弟弟大徹大悟:麵對塵世,唯有慈悲。
對於永遠無法掙脫命運的人來說,還有什麽比慈悲更可貴?對於那些無法沐浴在自由的陽光中的人們,還有什麽比慈悲更能撫慰心靈?沒有慈悲,你將溺斃在那如潮的苦難中。
顯然,《慈悲》寫的絕不僅僅是一家工廠,而是隱喻了一個時代,乃至一種文明的結構方式。在這個文明中,人很少被看成是不可動搖的、最根本的因素,隻有得了利益的群體為了永遠得利,或者那些沒得到利益的群體為了顛覆秩序,他們才不約而同地把人搬出來做藉口,我們始終缺乏一種悲憫,始終不肯站在人本身的立場上去看問題。
一百個人的逝去,不是一乘以一百那麽簡單,因為每個一都不同,是水生+師傅+玉生+水生的弟弟……一直加下去,加到一百。一個人的死去,就是一個世界的熄滅,就是他全部的情感、愛、記憶、理想與惦念的幻滅,可問題是,當幾萬人、幾十萬人的生命都被輕易地抹去時,那麽,連一百都成了小數字,一又算個什麽呢?
我們每個人都是一,或者,每個在路上混丟了夢的人,每個被迫忘掉曾經自己的人,都該來看看這本小說。至於為什麽,你懂的!
原文地址:https://www.bidushe.com/article/27142.html